 專訪
專訪
鹿比∞ 吠陀新作專訪:人生隨處皆是到不了的《彼岸》
這是他的第三張專輯。從《重力與恩寵》一路走來,你可以看見他的改變。
《彼岸》象徵永遠無法到達的二元對立
「並沒有人生上的巨大事件。我接觸了一些佛經、一些電影,另外就是工作經驗。」鹿比吠陀告訴我《彼岸》是怎麼動念產生的。

在獲頒金音獎後,鹿比吠陀找到全職音樂工作,因配樂開始品嚐為人作嫁的甘苦。「我想的和導演想的,總是有那麼點不同。音樂和畫面,總是有層衛生紙般薄的間隔存在。」他發現人們的品味不同,觀點不同,就會有隔閡。這些隔閡看似微小,事實上永遠跨越不了。
鹿比吠陀認為彼岸不必然非到生死才能看見。只要人們心中覺得有個更好的方向,二元對立的彼岸就自動出現了。
他舉了北野武的《阿基里斯與龜》說明這個概念。「裡面的藝術家一直在追逐著著風格,想進入殿堂。但每當他快追到時,那個風格就沒落,他永遠進不去。《彼岸》有這個含意,它是一個永遠無法到達的境地。」
《彼岸》是自己也想重複聆聽的專輯
儘管配樂工作的艱困讓鹿比吠陀感覺「永遠無法到達」,但其中經驗也成為他的養份。
「之前的專輯我並沒有考慮歌與歌的關連性。但這次,我希望聽的人能從頭聽到尾,跟專輯走完整個故事線。」鹿比吠陀試圖讓《彼岸》變成一部電影,更希望《彼岸》值得再三回味,讓人們看見他的配樂能力。

他坦承先前大獲好評的專輯雖然很酷,但自己卻無法再三聆聽。為此他這次費盡巧思。「因為我也想聽自己的作品第二次。」他說道。
「譬如〈陰陽〉就花了我一個月。」鹿比吠陀表示專輯開頭的〈陰陽〉原本該是一首八分鐘、五十軌、充滿弦樂的作品。一個月後它只剩58秒,軌數更一度被刪減到五軌,而後才用Reverse慢慢擴充到20軌。「我希望別人聽到一個故事,所以開始和結尾很重要。」
「所以這都是我在創作中慢慢整理自己,而不是在一開始就設計好。」鹿比吠陀說明創作過程是有機的。「並不是我一開始就想要20軌,或一開始就想要二元對立。我是一邊修剪,寫到〈色相〉,才確定一整篇會長這樣。」

一旦確立「二元對立」這項主題,鹿比吠陀便應用大量的Reverse呼應它。「專輯中的〈曼珠沙華〉(又稱彼岸花),就是最能代表『二元對立』的植物。他們的花和葉子永不相見,但都來自同一個根。就像Reverse的兩個聲音都是同一個來源。」鹿比吠陀如此詮釋Reverse特效對於《彼岸》的重要性。
至於把音軌數量限制在20軌內,則是因為希望作品經得起聽。「我之前也嘗試過疊大量軌,但以技術來說這種作法很難混得漂亮好聽。因為聲音跨了太多頻率,差別又太小,交給專業人士處理時他會很困惑,於是又產生了另一個彼岸。」鹿比吠陀笑稱製作《彼岸》的過程中只要看到音軌出來肥肥的,他就會打掉重做;因為肥肥的表示歌曲沒動態,一定不耐聽。
封面淡雅清新恰如其份點出醍醐味
在《彼岸》曲目上公佈的合作歌手有三位:Toshiya Fueoka、林泓伸、黃宣。問到為何三位對象都是男性,他回答「既然這次的主題是二元對立,我這次的音樂又很女性化,人聲就必須是男的。」找來這三位男聲,為了要頂住「靈魂上的頻率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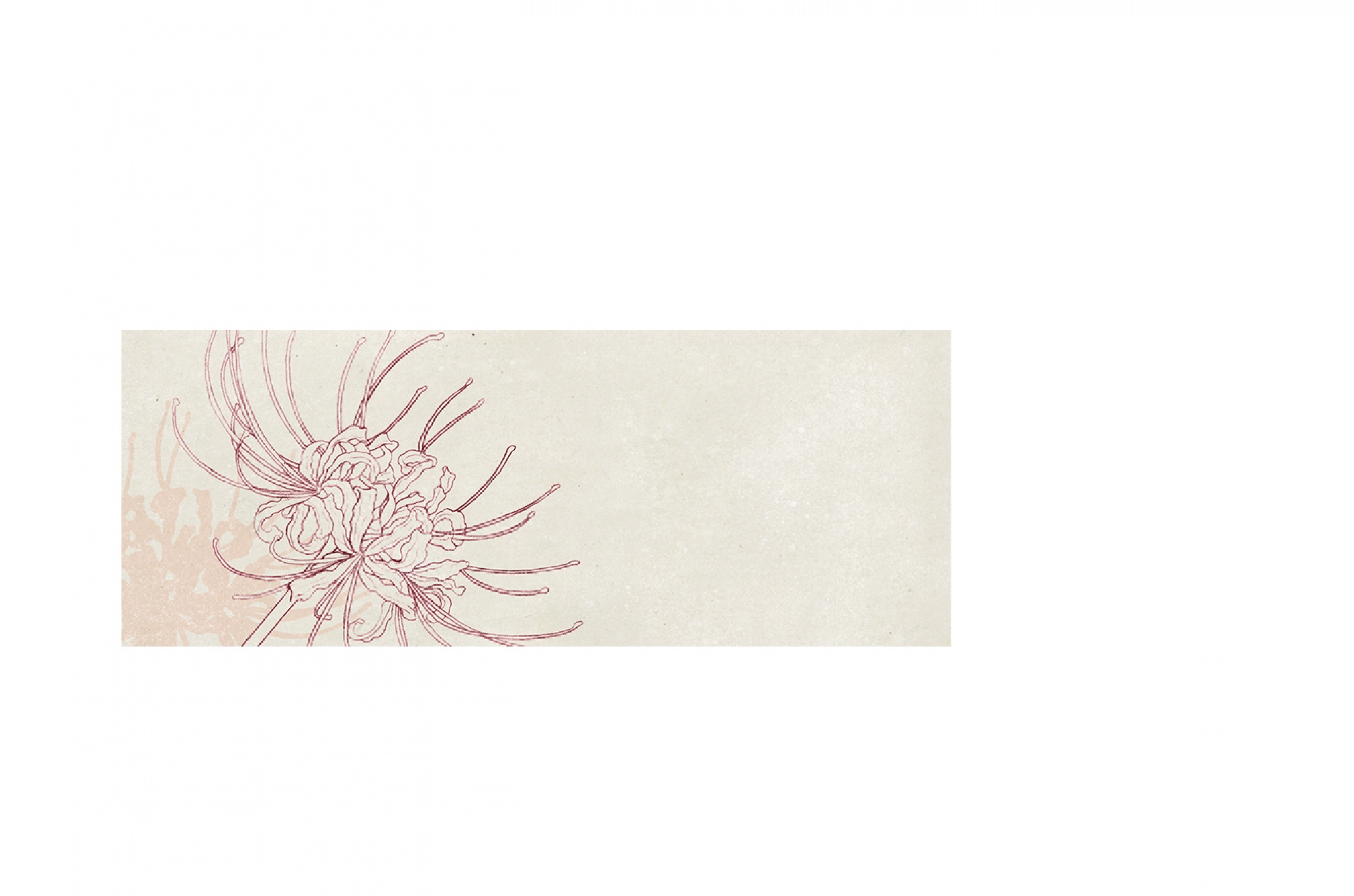
除了合作歌手以外,《彼岸》的封面是另一個吸引人的大亮點。順著專輯揭露的插畫家資訊,我們點進YUN CHUAN Illustration的粉專。映入眼簾的,是一系列清新淡雅的花草畫。每張圖都精緻得讓人再三玩味。相同的悸動在鹿比吠陀點開瞬間一定也感受到了吧。
「他畫的花介於寫實和抽象之間,色彩運用也到了一個境界。」鹿比吠陀研究所攻讀東方美術史,一談到畫就打開了話匣子。他解釋YUN CHUAN的繪畫如何巧妙的結合了西方藝術風格、日本浮世繪風格,還巧妙帶上台灣日治時代的膠彩畫氣息。
細看YUN CHUAN為《彼岸》繪製的插畫,能感受它這些圖片就像是放在奶油蛋糕上的甜中帶酸的草莓,恰如其份提點出整張專輯的醍醐味。在《彼岸》他的表現優秀,讓我訝異為何他先前從未出現在大眾視野中。

「我是去翻作品集翻到的,不是靠別人介紹,」聽到這句話我笑了出來,這根本是土法煉鋼,但這也真的是鹿比吠陀慧眼識英雄。「這麼厲害的繪師竟然沒有紅,我覺得還蠻荒謬的。他是個很內向的人,不太懂得行銷自己。」
鹿比吠陀談到YUN CHUAN在英國Kington學本格派的插畫,作品卻非常東方。「而我的作品受了佛經啟發,出發點是很東方的。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插畫家能又東又西。」說到底,連插畫家的挑選也是鹿比吠陀為了配合主題,精算的結果。
遠離焦躁,和痛苦和平共處
從《重力與恩寵》走過《蒼白》,再進化到《彼岸》,鹿比吠陀的聲音少了不安、焦躁、狂爆與撕裂,取而代之的是穿透而來苦甜。即使像〈悲愴〉這樣強烈的標題,聽來也像是充滿憐憫的溫柔端詳。
我們聊到曾經(也許現在依然)被稱為暗黑魔女的鹿比吠陀。他說那畢竟是標籤。人們太習慣以標籤理解他人,以致忽略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真實改變。
「我在做第一張專輯的時候心中充滿煩惱,精神狀態很差。」他解釋《重力與恩寵》所反應的心境。「我在生活和感情上有很多煩惱,未來也讓我煩惱。我那時還不確定要不要以音樂為生,工作是英文老師,我很不快樂。覺得好像所有事情都不對。」

高中時鹿比吠陀創作了小說《史考特醫生》,一舉拿下首屆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青龍獎的首獎。原本自己和父母都以為未來會以文學謀生,但他的成長打碎了這個夢想——他注意到了「身體」和「性」。他說自己很晚熟,高中時基本無性/性別,也痛恨奇幻小說中出現肉體的味道,對性/性別的不安讓他無法繼續寫純粹的奇幻小說。
他也嘗試著轉換題材,閱讀與創作純文學,結果反而被更多的性壓得喘不過氣。於是只能放棄寫作。
他笑自己相當於折斷了寫小說的手。但再怎麼看,這個人畢竟天生就該寫些什麼吧。把自己硬塞進不是自己的工作,只會催折靈魂。
「我曾經考慮把筆拿起來繼續寫,但發現又開始寫的話精神狀態會很差。因為寫作是一件很誠實的事,你陷入了痛苦,要寫它,你就得命名那個痛苦。痛苦會變得有聲音有畫面甚至有文字,到最後沒有辦法收拾。」他嘆道。「在音樂創作中,你比較容易和情緒保持一個安全的觀眾席距離。文字實在太具體了,太痛了。音樂比較好。」
音樂讓鹿比吠陀天生屬於創作的靈魂能繼續創作。也許就這個角度來說,是音樂拯救了鹿比吠陀。「我現在終於可以再重新開始寫東西了。目前我也在上劇本課,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寫自己的電影腳本。」十七年鹿比吠陀折斷了寫小說的手,也許終將痊癒。
所以,我在《彼岸》感受到的變化,究竟是什麼呢?鹿比吠陀說那是妥協,對痛苦與困惑的根源不再追究,終於妥協。我感受那是超越,就像他說曼珠莎華的花與葉其實來自同樣的根,無須對終不相見彼此傷懷。
對於《彼岸》的理解,我和鹿比吠陀終究也成了兩個相望的彼岸。但從我這頭望去,至少可以確定的是,鹿比吠陀終於能與痛苦和平相處了。


